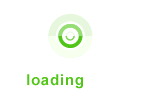核心提示: 陈凯歌说程蝶衣必须死,唯有死才能让他不朽,这句话早在千年前在虞姬身上就得到验证,她若不别霸王,世人不会记得她的坚贞和美丽;可是这句话十年后在张国荣身上也得到了验证,试想哥哥若年过古稀,还会不会有人怀念他曾经的风华绝代和天赋异秉,关于他穷其一生努力要让世人理解他的愿望会不会...

当年梅兰芳在纽约百老会剧院完美谢幕的时候,他成了中国国粹的神;如今中国电影在市场野心与个人风格之间尴尬求存的时候,多年前的《霸王别姬》渐成无法复制的风景,陈凯歌也就成了中国电影的神。然而《无极》的意外失算又再次印证了电影难以摆脱的法则:绝对没有神,观众是绝对的上帝,他可以把你捧上神坛,也可以让你跌入深渊。
其实一个人的才华只需要一部优秀的作品就可以让全世界记住他。比如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如让黑泽明不朽的《罗生门》,比如使布努艾尔成为超现实主义符号的十七分钟短片《一条安达鲁狗》。当然也有的人是无冕之王,比如无缘诺贝尔的米兰昆德拉,以及在《无间风云》之前无缘奥斯卡的马丁斯科塞斯。所以不是《梅兰芳》让陈凯歌回来了,是他一直都在。
《梅兰芳》和《霸王别姬》,不一定非比较不可,也不是想看后者能不能超越前者。而是想知道同样关于国粹艺术,同样一个戏子的一生,是虚构的美还是写实的美。答案似乎早已成定论。原因很简单:创作受限。传记片总不如故事片那样挥洒自如,最重要的是,传记片要把人变成神,而故事片只是把作者的思想变成人。这就是为什么往往传记片看起来比故事片还要戏剧化,而有的故事片倒象是纪录片的缘故。鉴于对一个伟大人物生平事迹的复述,创作方要作多方顾虑,要改编,一改就会被诟病。所以即使《梅兰芳》不能超越《霸王别姬》,陈凯歌依然是中国最顶级的导演。
一、小说和传记
《霸王别姬》有一部优秀的小说作为蓝本,小说本身天马行空的特性注定了故事必然充满戏剧性。程蝶衣与人群,与环境,与时代,无不充满动人心弦的偶然。让一个人的传奇穿越几个时代而能善始善终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是程蝶衣不是特定的某一个人,他是芸芸众生中无数命运相似的人,平凡卑微,另类如斯,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于浊世中保留一颗纯粹的心,任凭周围兵荒马乱、风云变幻,不为所动。悲伤生生不息,蝶衣的悲剧是虞姬千年后仍未停止的哀伤。一个泣血的故事成全了一部伟大的电影,虞姬的繁华落尽后,是陈凯歌电影传奇实实在在的粉墨登场。
《梅兰芳》的蓝本是梅家后人为真实人物所写的传记,而现实又总难免尴尬。梅兰芳在属于他的时代里就已经成了神,百年后的电影人只能再次放大至接近完美,所以必须不断修补残缺的现实,重新编剧,直到高山仰止。当电影里所有的人和事都为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梅兰芳而与原型不符甚至不完整时,传记就不再是传记,而是传奇。黎明对梅兰芳的刻意模仿在那些人工雕琢的环境中反而显得格格不入。
二、程蝶衣和梅兰芳
他们同样纯粹,为京剧而活。只是程蝶衣的纯粹更彻底,他少了梅兰芳肩负的使命,他是为虞姬为霸王而活的,他无法选择命运,却能令灵魂始终不染纤尘,在纷乱的尘世中保留对爱情和京剧的忠贞。而梅兰芳自从偷看了大伯的信之后,他的肩上就有了一副无形的担子,这副担子在十三爷爷去世后更加沉重,他要提拔伶人的地位,让京剧不朽,要作多方隐忍,甚至舍弃最爱的女人,所以他的纯粹中难免渗入世故。
当性别错位后,程蝶衣与虞姬渐渐融为一体,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愁,袁四爷说那是转世的虞姬,其实程蝶衣早已把自己当成了虞姬,他的霸王就是从小呵护他的师哥段小楼,他的人生就是一出戏。梅兰芳不同,他也演过《霸王别姬》,不过虞姬只是他众多角色中的一个,他不会迷失,在台上他比女人还要女人,在台下却是堂堂须眉,他很清楚京剧仅仅是艺术,他的人生不是京剧,而是为京剧的命运而奋斗。所以虞姬的剑最终吻上了程蝶衣的脖子,而梅兰芳却是带着京剧走出了国门。
三、张国荣和黎明
梅兰芳不是程蝶衣。张国荣演程蝶衣,黎明演梅兰芳,他们的气质分别与角色相似。作为导演,陈凯歌能够决定的只有这一点,至于演得好不好,大部分还是要看演员本身的功底和天份。最近铺天盖地的评论说应该让张国荣演梅兰芳,其实那仅仅是人们对哥哥无以复加的思念情绪,就算哥哥在世,相信陈凯歌也会选择黎明,因为气质是与生俱来的,黎明本身的高大儒雅很贴合梅兰芳的文人气质,不需刻意塑造。
程蝶衣是披着男儿身的女娇娥,张国荣从眼角眉梢到精神内核都把握住了这一点,蝶衣是谁?无从可考,他是蝶衣,蝶衣就是他。所以他演活了程蝶衣,即使他后来置万千宠爱于 不顾而纵身一跳,多年后人们痴痴恋着的还是“蝶衣,蝶衣……”。黎明一贯的儒雅和木讷演起梅兰芳来不用过分雕琢,但是梅兰芳毕竟是历史人物,且自身的艺术气质是长期修炼的结果,现代感十足、非京剧专业出身的黎明要完全再现他的神韵是很困难的。而且电影中梅兰芳身边的人物都已经戏剧化,有的甚至面目全非,黎明过多的模仿原型反而不谐调,这种类似于欲说还休的窘境难免让人抱憾。所以人们看到的还是黎天王,而不是梅大师。所以黎明的梅兰芳不如张国荣的程蝶衣出色。
四、段小楼和孟小冬
段小楼是小说中的段小楼,孟小冬是历史上的孟小冬,不是五四青年版的章子怡。把这两个人名放在一起有点意思,因为他们至少有一点很相似,就是非常现实,艺术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把他们放在一起说,既是对程蝶衣爱情的尊重,也是对孟小冬婚姻的尊重,而这两样在当时的时代环境里是被世俗所不容的。有懂程蝶衣的人,他们是日本军官青木、恶霸袁四爷;也有懂梅孟之恋的,他们是冯六爷以及梅党们,可惜他们最后都还是不得不屈从于现实而放弃艺术环境。
段小楼没有错,他有现实中的“虞姬”,就是菊仙,他对蝶衣除了呵护还是呵护,虽然后来在文革的闹剧中连兄弟的情谊也被撕裂得荡然无存,程蝶衣一厢情愿地爱上段小楼,使悲剧无须跨越长达半个世纪的演变就已经注定。孟小冬与梅兰芳也因戏结缘,现实中究竟谁爱上了谁已不重要,银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一段柏拉图式的爱情,国际章一副有心计的女学生样,超级粉丝刺客的偶像也从孟小冬变成了梅兰芳,这样处理对孟小冬究竟是拔高还是忽略值得商榷,但至少可以肯定孟小冬之于梅兰芳的影响是很深的,否则有洁癖的梅家为何不写更清白的刘喜奎。
五、那坤和六爷
金牌配角英达会继续客串是毫无悬念,但是比起《霸王别姬》中的戏园子老板那坤,英达在《梅兰芳》中的戏份明显加重,他演一个银行家冯六爷,为梅兰芳赴美演出提供资金,也是“梅党”的重要成员之一,现实中的原型是谁并不重要,问题是陈凯歌的严肃电影里需要这么个和稀泥的角色,他也确实为影片增色不少。《霸王别姬》是由表皮悲到骨子里的悲剧,英达使人想到英若诚,英若诚又使人想到《茶馆》,戏园子老板又让人想到《茶馆》里的王利发,这种悲凉的圆滑使整部影片的基调更加绝望。《梅兰芳》是充满希望和力量的电影,英达继续深藏不露地圆滑,却是善意温暖的。
六、少年蝶衣和少年畹华
程蝶衣的少年时代和梅兰芳截然不同,从被硬生生截去第六指,到为“我本是男儿郎”吃尽皮肉之苦,再到被张公公亵渎,蜕变的过程充满苦难,尹洽饰演的少年蝶衣让人看着莫名地心酸。相反,余少群饰演的少年畹华扮相俊美得脱离原型,他的责任在于表现舞台上的梅兰芳,少年畹华也遇到过类似的骚扰,但他能够对他们挥出愤怒的大巴掌,可是程蝶衣不能,他没有主张,只能在冷酷如斯的周遭中对着一丝半缕的温暖念念不忘。
少年蝶衣未及卸妆,身着被张公公抓烂的戏装仓皇逃回。少年畹华的最后一个镜头也是未及卸妆,但他是为了尽快见到打擂之后的十三爷爷,脸上的脂粉掩饰不住身为男子汉丈夫的责任感,他比程蝶衣幸运得多,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戏子的身份,除此之外,命运完全两样。也不明白李碧华既是写张国荣,却为何要把他写得如此苦命。再试想一下,若让李碧华也为梅兰芳量身定做一部小说将会是怎样的。
七、主角与配角
《霸王别姬》主角是真正的主角,光芒能盖过配角,所有镜头全部围绕一个程蝶衣,张国荣亦是懂得镜头的人,所以,虽然全剧中包括程蝶衣在内,没有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小楼现实冷酷,菊仙庸俗精明,那坤圆滑,袁四爷懂艺术但亵渎艺术,青木懂京剧但是不得不放弃……但是整部影片下来,你会满脑子的程蝶衣、虞姬。
《梅兰芳》几乎把镜头对准了大部分配角,而演员们的表现也让这些角色十分鲜活,比主角梅兰芳更让人印象深刻,如十三燕、福芝芳、费二爷等等。只是因为《梅兰芳》里的人物都有原型可考,所以再鲜活也难免被诟病,比如孙红雷饰演的邱如白,与原型齐如山先生是有很大出入的,齐如山是一位潜心钻研京剧艺术的严谨学者,而邱如白就势利了很多,整个一经纪人加超级粉丝;十三燕的原型是大师谭鑫培,王学圻的表演是非常出色的,除了少年畹华的惊艳以外,前半场的亮色基本因他而起。八、时代背景
电影《霸王别姬》能够超越原著是因为陈凯歌很好地渲染了原著中的时代背景下的人生百态,并在恍惚的氛围中强调人物命运的不可逆转以及程蝶衣的偏执。从民国到抗日再到文革,所有的事物都变了,只有程蝶衣始终没有变,张公公是封建王朝制度丑恶的浓缩,而人性的丑恶在文革中被放大到极致,一直隐忍的程蝶衣也被激怒了,可是他没有伤害他的霸王,他只是像所有的凡人一样牵怒于夺爱的菊仙。
梅兰芳本人的经历也跨越了多个时代,从甲午战争到文革以后,但是电影只是选了与《霸王别姬》相似的几个背景,如民国和二战,也没有提到文革。经历过这么多,如果说程蝶衣是涅槃的过程,那么梅兰芳至少有一个修炼的过程。可是电影只选了他一生中最为华彩的几幅篇章,让梅兰芳的人生况味被大半省略,使整部影片稍嫌散乱。看来传记片是全世界导演的难题。托德海因斯拍到现在,在《我不在那儿》中为了标新立意,让一个熟悉的鲍勃迪伦变成六七个人,电影果真因此而好看了吗。
九、关于结尾
陈凯歌说程蝶衣必须死,唯有死才能让他不朽,这句话早在千年前在虞姬身上就得到验证,她若不别霸王,世人不会记得她的坚贞和美丽;可是这句话十年后在张国荣身上也得到了验证,试想哥哥若年过古稀,还会不会有人怀念他曾经的风华绝代和天赋异秉,关于他穷其一生努力要让世人理解他的愿望会不会实现,是个问题。失去后才知道珍贵。这条规律绵延了几千年也没有人能重视它,总是不断地拥有,不断地失去,不断地悔不当初。
但是对于电影艺术而言,略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什么虚构的悲剧远比写实的正剧更黑色更让人久久回味。